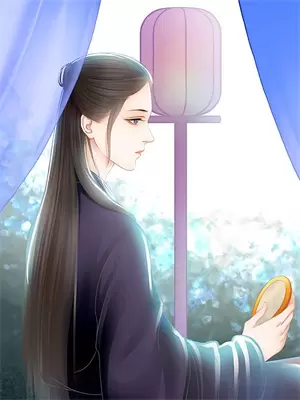1 重生悬崖边赵娜在朋友圈晒出订婚戒指向我宣布:“吴越,我怀了非洲酋长的孩子,
下个月就去当太子妃。”机场里我拼命阻拦她离开:“那人是个骗子!
嫁给他你会被骗去当生育机器!”她愤怒地给我一巴掌骂我自私:“你就是嫉妒我的幸福!
”婚后我陪她在小出租屋里生活,她日日怨恨我毁她富贵。
直到发现那个“酋长”在朋友圈晒他真正的贵族生活后,
她在我们的周年纪念日将我推下山崖。“都怪你!我本可以过那种生活!!”再睁眼,
我回到她第一次当众炫耀“非洲太子爷”礼物的咖啡厅。前世血淋淋的悬崖在脑中闪过,
我微笑着将手中咖啡递给她。“抱歉,是我不配,祝你幸福。”2 虚假太子妃这一次,
我亲眼看着赵娜欢天喜地奔向死亡。“吴越,你看!”赵娜的声音刮着我的耳膜,
尖锐、得意,尾音带着一种刻意炫耀的钩子。她把手机屏幕几乎怼到我眼前,
上面赫然是一枚极其夸张的“钻戒”——大得离谱,切割粗糙,
在咖啡厅惨白的灯光下反射着廉价的、塑料般的光泽。手指在图片上方滑动,
几张精心挑选的合影刷出来。照片里,赵娜依偎在一个高大、黝黑的男人身边,
笑得一脸沉醉。那男人穿着花哨得像裹了一身霓虹灯的“传统服饰”,
脖子上挂满沉重的金色链条,咧着嘴,露出一口过分洁白的牙齿。“杨天佑送我的订婚戒!
好看吧?”赵娜收回手机,抚摸着屏幕上那颗闪烁的石头,指尖因为用力甚至有些微微颤抖,
透着一股病态的亢奋。她抬起下巴,轻蔑地瞥着我,像是看着一件亟待处理的垃圾:“吴越,
我怀上了杨天佑的孩子,以后我跟他就是一家人了!下个月初的飞机,
我要去他的国家当太子妃!”咖啡厅劣质人造皮革座椅在身下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空气里弥漫着香精勾兑的焦糊味、廉价咖啡的苦涩,
还有赵娜身上那款廉价香水过于甜腻的浓香。我看着她,仿佛在看一出荒诞又惊悚的哑剧。
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她亢奋的炫耀,那枚假的离谱的“钻石”,
那个黑皮白牙、叫杨天佑的诈骗惯犯,还有她那“太子妃”的春秋大梦。
前世那种撕心裂肺、心急如焚的情绪,像海啸一样瞬间退去,只剩下冰冷死寂的海床,
带着劫后余生的麻木和刺痛。原来它一直在这里等着我。这座悬崖。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它只是隐没在我盲目的付出里。真蠢啊,吴越。你用命,
只教会自己一个道理:爱可以粉饰地狱,却救不了奔向地狱的人。‘娜娜,你别走!
’ 那是前世的我,声音嘶哑得像在泣血。‘别拉我!你放开!
’她的指甲狠狠抓过我的手背。机场广播冷冰冰地播报着航班信息,
她的尖叫盖过一切:“吴越,你够了!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清楚?你就是自私!
你就是看不得我幸福!你就是个又穷又窝囊的可怜虫,嫉妒我找到了真爱,
找到了杨少这样的豪门!”‘他不是什么太子爷!那是个骗子!
他专门骗你这样的女人过去当生育机器!你跟他走会被卖了都不知道!
’换来的是狠狠一记耳光。清脆响亮。那是前世她对我长达六年无休止怨恨的开端。
那一巴掌和她之后日日夜夜无止尽的抱怨、咒骂,
最终积累成崖顶上那只带着滔天恨意、重重推向我后背的手。‘都怪你!
我本可以过那种生活!!’她那张因怨毒而扭曲变形的脸,是我坠崖时看到的最后景象。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身体撞击嶙峋山石发出的沉闷碎裂声……咖啡厅嘈杂的人声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模糊地涌上来。赵娜还在喋喋不休,
涂着廉价亮片指甲油的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子:“……看到了吧?这戒指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杨少随手就给我了!你呢?吴越,你除了给我那些地摊货,除了没完没了地拦着我追求幸福,
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辈子就是个穷酸的命,别拖累我!”她那鄙夷的目光像冰冷的刀子。
前世,我就是被这样的眼神和她日复一日的‘穷酸’、‘窝囊’、‘耽误我青春’的指责,
一点点磨掉了最后一点自尊和反抗的力气,成了跪在她脚边摇尾乞怜的一条狗。我抬眼,
迎上她刻薄又轻蔑的眼神。胸腔里那颗心早已被摔碎过一次,现在只是被冰块冻住了,
不再跳动。我甚至闻到了风里夹杂的、属于前世的血腥味。
3 冷眼旁观咖啡厅廉价而浮夸的吊灯在头顶闪烁着令人晕眩的光晕,
那枚巨大塑料钻戒在她指间廉价地反光。刺得我眼睛生疼。“嗯,
”我发出一声轻飘飘的单音,嘴角却用力勾了起来,一个弧度僵硬却又异常清晰的微笑,
“看到了,很漂亮。”赵娜炫耀的表情僵了一瞬,似乎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娜娜,
” 我听到自己清晰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像在念一段与我无关的台词。
我把面前那杯一口未动、杯沿还沾着廉价奶沫的咖啡,轻轻朝她的方向推过去几寸,“抱歉,
是我配不上你。”她的眉头骤然拧紧,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眼神里全是错愕和狐疑,
似乎在辨认我是不是在玩什么新的花样。我看着她,笑容加大,
像一个僵硬的、排练过千百次的面具,清晰地露出牙齿。“祝你幸福。”我说。
这四个字轻飘飘地出口,却在我空荡荡的心腔里撞出巨大的、沉闷的回响。
我的灵魂仿佛被无形之手“哗啦”一声撕开——一半悬浮在半空,
冰冷而漠然地俯视着眼前的一切;另一半则深陷在那绝望的崖底,被尖锐的碎石刺穿着。
时间在断裂。咖啡馆嗡嗡的噪音变得遥远模糊,
赵娜那张涂得五颜六色的脸孔也虚化成刺目的色块。我身体里的那个吴越正在消失,
那个为了爱一个人可以丢掉尊严、献祭生命的蠢货……马上就要彻底断气了。赵娜愣住了,
脸上的得意和轻蔑如同劣质颜料一样迅速剥落,露出底下的空白和一丝惊慌。
她像是被我这句过于平静的祝福烫到,下意识地缩回了指着我的手。“你……你什么意思?
”她的声音拔高了,又尖又硬,试图用刺耳的气势来掩饰此刻的心虚。“就是你听到的意思。
”我平静地回答,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心口那个洞,正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
再多的情绪也填不满它了。“你想要富贵荣华,你想要太子妃的生活,我祝你……如愿以偿。
”我刻意放慢了语速,“如愿以偿”四个字像淬了毒的钉子,
一个个钉在我们之间彻底坍塌的过去上。赵娜张了张嘴,大概是想习惯性地反驳、讥讽,
或者再用“穷酸”、“没出息”这种话来攻击我。但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也许是我的表情太平静,太平静了,平静得让她第一次感到一种近乎惊悚的不安。
那不再是愤怒、嫉妒,也不是卑微的挽留,那眼神里空无一物,只剩下冰冷的死寂。
这种死寂比任何激烈的反驳都更让她无所适从。我看到她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对,就是失落。她习惯了掌控我的情绪,看我像个小丑一样被她摆弄,哀求,愤怒。
这种彻底失控的局面,这种被她认定是蝼蚁的存在突然主动宣告退场的姿态,
打破了她熟悉的剧本。这种失落很快被一种更强烈的恼怒和固执取代。她挺直了背脊,
下巴重新抬高,如同一个即将就义的烈士,为了捍卫她那可笑的虚荣和所谓的“爱情”。
“哼!装什么装!”她冷笑一声,猛地抢过桌上那杯我推过去的咖啡,动作粗鲁,
差点把里面的液体晃出来,溅了几滴在她那身鲜艳得扎眼的裙子上。她看也不看那些污渍,
眼神像刀子一样剜着我:“吴越,别以为你搞这出以退为进我会心软!告诉你,没用!
收起你那些可怜的自尊心吧!”她又深吸一口气,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更像是在向我宣战:“我跟杨少,是真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下月初八的飞机,
谁也拦不住我!”她端着那杯被我推过去的廉价咖啡,像拿着一个象征她胜利的战利品,
狠狠地瞪着我,仿佛要把我最后一点尊严彻底踩碎。“我赵娜,”她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宣告,
目光掠过咖啡馆里几个悄悄投来视线的看客,“这辈子注定是要当王妃享福的命!
你这种穷酸学生,活该打一辈子光棍!以后我朋友圈里晒的豪宅游艇私人飞机,
你可别眼红得掉出来!看了就心烦!以后别联系了!删掉吧!”咖啡厅里灯光惨白,
照得她脸上涂抹厚重的粉底显得更加粗糙。她不再看我,像个骄傲的斗鸡,昂着头,
拿着那杯冰凉的廉价咖啡,踩着至少十公分的劣质高跟鞋,扭着她那并不纤细的腰肢,
“嗒嗒嗒”地走出了咖啡馆的玻璃门。光怪陆离的霓虹在她背影外面闪动。很好,赵娜。
飞吧。4 放手搏这一次,我绝不阻拦。我看着她走进那扇旋转玻璃门,
汇入外面街道车水马龙的光影中。背影挺得笔直,像个英勇就义的战士。
服务员端着咖啡经过,浓郁的香气刺得我鼻腔发酸。原来绝望到极致,
嗅觉反而会变得异常敏锐。那扇厚重的玻璃门旋转了一下,哐当一声轻轻合拢,
隔断了外面喧嚣的车流声和人潮涌动。赵娜消失了。
我维持着那个僵硬的、被强行扯出来的笑容的肌肉,一点点放松下来,
脸部的神经却绷得更紧,扯得一阵发疼。
直到那杯廉价的咖啡里最后一点点残存的冰块融化的声音似乎都清晰可闻,
我才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将目光从空荡荡的玻璃门口收了回来。
“嗡——”桌上的手机屏幕适时地亮起,在昏暗的角落光线里有些刺眼。
屏幕上跳动的一个名字——黄胖子。这胖子的电话,还真是……掐着秒表来的,
和前世一模一样。他是杨天佑那个诈骗团伙的“外围”掮客。前世的我,
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开始疯狂地搜集关于杨天佑的一切蛛丝马迹。我按下了接听键。
“喂?吴越?”黄胖子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急迫感,充满了油腻的关切,
“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我听人说…刚在蓝湾咖啡看见你跟赵娜了?…你俩…吵吵起来了?
动静不小啊?为了那个…那个什么…杨什么佑?那非洲阔少?”前世的我,
听到这“非洲阔少”几个字,肺管子都要气炸了,只觉得气血翻涌,恨不得隔着电话吼回去。
可现在,只有一阵一阵冰凉的麻木感贴着脊椎骨往上爬。我甚至扯了扯嘴角。“没有。
”我的声音很平,没有任何起伏,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实,“结束了。
”电话那头明显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消化我这异常平静的反应。“结…结束?
”黄胖子显然愣了一下,“不是…吴越,你别冲动啊!
赵娜她…”他的语气像沾了油的水般油腻地打着滑:“小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床头吵架床尾和嘛!再说了,那位杨少,啧,那可是非洲某部落实打实的继承人,
标准的王子!钻石金矿土地,你想想!人家赵娜也是想奔个好前程,姑娘家家的,
你体谅一下…”“我没冲动,”我打断他,声音依旧没有任何温度,“她说她要去当太子妃。
我跟她说,我配不上,祝她幸福。就这样。”电话那头的沉默更长了些,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这就…放弃了?”黄胖子再开口时,那股假惺惺的关切淡了不少,
透出一种隐藏不住、近乎本能般的探询与算计。那才是我认识的那个真正的黄胖子,
靠舔舐别人的痛苦和踩踏弱者来捞油水的货色。“不是…兄弟,你真甘心?好几年的感情啊!
就被那黑小子…咳…就被那杨少撬走了?你就一点不想再试试?男人嘛,
有时候该拉下面子就得拉下…”“甘心?”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像是在咀嚼一粒没有任何滋味的沙砾。舌尖上泛起一阵铁锈般的腥甜。
那是前世坠崖时灌进口鼻的尘土味。“胖子,”我对着话筒,声音轻飘飘的,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隔着时空与前世的自己对话,用词冷漠得陌生,“你告诉我,一个人,
怎么去拦一匹非要拉着车撞向悬崖的马呢?”前世的我,就是那匹被蒙住眼睛的马,
只看到眼前一点虚假的情爱幻光,最终车毁人亡。电话那头彻底沉默了。
黄胖子大概被我这种近乎冷血的态度震住了。
这完全不符合他熟悉的那个“深情舔狗”、“愤怒怨夫”吴越的形象。
“行吧…行吧……”他终于含混不清地应了两句,语气复杂,有探究,有狐疑,
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他似乎没能从我这里得到预期中的激烈反应、痛苦倾诉或者被羞辱后的愤怒求助,
这让他这种习惯了从别人痛苦中牟利的蛆虫感到无所适从。“你…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唉,
也好,也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他说着连自己都不信的屁话,匆匆挂了电话。
“嘟嘟嘟……”忙音传来。5 孤注掷咖啡馆的嘈杂声浪重新涌入耳朵。咖啡已经彻底冷了,
上面浮着一层冰冷的油脂。黄胖子这种货色,就是苍蝇,哪里有裂缝就往哪里钻,
前世他没少在我这里挖赵娜的消息。他现在打电话来,绝非善意。
更大的可能是杨天佑那个团伙需要确认,我这个“障碍物”到底移开了没有。
我看着手机上那个名字一点点暗下去。删掉?不,留着他。苍蝇也是线索。说不定,
当赵娜那头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这张牌还能有点用。离开咖啡馆时,
外面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深秋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钻透了我单薄的外套,直透骨髓。
我拿出手机,犹豫了片刻。屏幕解锁,那个熟悉的暗红色应用图标——期货APP。
手指悬在图标上,指尖冰冷。这玩意儿像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横在我眼前。
前世的记忆碎片如幽灵般闪现:某个财经网站角落里极其不起眼的一则快讯,
关于非洲某小国因雨季反常提前结束导致可可豆预估大幅减产的消息。当时正经历丧父之痛,
对这消息根本没有留意。但几个月后,全球可可期货价格……疯狂暴涨。
时间是……我快速调出日历APP。对!就是现在这个月中旬前后爆出来的消息!
距离正式减产公告还有……一周!时间点完全吻合。七天时间。这七天,
就是我重获这条命之后,唯一能抓住的稻草,唯一能撬动命运的支点。一股从未有过的狠劲,
混合着对悬崖底部那彻骨寒冷的恐惧,猛地涌上心头,激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不能犹豫了。
要活下去,要活得比赵娜那个“太子妃”风光,就得用这七天,赌上一切!银行卡里的余额,
像一个冰冷的讽刺,刺眼地显示在ATM机的屏幕上:¥17,843.56。
那是前世的“我”这个蠢货,省吃俭用抠出来,准备存给赵娜买订婚戒指的钱。如今,
它是我唯一的本钱。我走进宿舍楼时,空气里混杂着泡面、灰尘和汗臭的沉闷气息一如既往。
推开自己那扇吱呀作响的门,一股熟悉的、属于前世的憋闷感扑面而来。狭小的空间,
堆满杂物的桌子,墙上贴着几张不知从哪本杂志撕下来的风景画——那是我和赵娜在一起时,
陪她去所谓“高雅”画展,她瞟了一眼说“这种垃圾也就挂穷学生墙上当宝”的画。
每一件陈设,每一丝气味,都像在无声地嘲讽:看啊,这就是你拼尽一切也未能挣脱的囚笼。
“哟,吴越回来了?嚯,脸这么臭?又被赵大小姐训了?
”同宿舍的周涛正叼着烟坐在自己的破桌子前打游戏,屏幕上光影闪烁。看到我进来,
他叼着烟,斜着眼瞥了我一下,语气里带着一种油腻的了然和幸灾乐祸。前世,
我没少在他面前抱怨赵娜,他已经习惯了看我“被训斥”后的狼狈样儿。我没理他。
前世的六年,这种廉价的“同情”和背后的讥讽,早听得耳朵起茧。我径直走到桌前,
拉开椅子坐下,目光冰冷地扫过房间里的一切。那只缺口的马克杯,
是赵娜嫌弃过的“洗都洗不干净的破玩意儿”;那个皱巴巴的劣质抱枕,
是她曾经说“闻着有股穷酸味”然后嫌弃地扔给我的。它们占据着我逼仄的生存空间,
散发着浓烈的失败者气息。周涛等了半天没见我接茬,自讨没趣地哼了一声,
注意力又回到了他那震天响的游戏厮杀声里。桌面角落,躺着一封皱巴巴的信,邮戳模糊,
是我老家镇上养老院的公章。手指带着点不受控制的微颤,将它抽了出来。
信封撕裂的声音在嘈杂的游戏音效里几乎听不见。展开那张印着养老院抬头的信纸,
里面只夹着一张照片和一页打印得歪歪扭扭的短信纸。照片上,是爸。
他坐在养老院光秃秃的水泥台阶上,身后是刷着绿漆的斑驳墙壁。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
简直要折成直角。那件洗得发白、衣领都快磨破的灰色旧中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