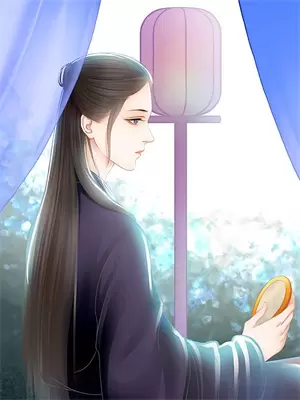午夜,像一整块被墨汁浸透的沉重丝绒,严严实实裹住了卧室。死寂中,
只有我身侧传来的、属于丈夫陈默那均匀而沉稳的呼吸声,如同潮汐,一下,又一下,
拍打着寂静的岸。他出差一周,今晚刚风尘仆仆地回来,
带着一身洗也洗不掉的、仿佛从地底深处掘出的陈腐泥腥味儿,倒头便陷入了沉睡。
我在这片浓稠的黑暗里,眼睛睁得发涩,却毫无睡意。一周的分离,
本该是温存小别的甜蜜夜晚,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却像无形的藤蔓,
顺着脊椎悄悄爬上来,缠得我心头莫名发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静默几乎要将我吞噬时,
床头柜上,我的手机屏幕骤然爆发出刺眼的白光,紧随其后的是撕裂寂静的尖锐铃声!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心脏猛地撞向喉咙口,几乎要从嘴里跳出来。谁会在这种时候打电话?
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我几乎是扑过去,
慌乱中手指在光滑的屏幕上滑动了好几次,才终于接通电话,颤抖着将手机贴到耳边。
“喂…?”听筒里没有寻常的问候。只有一种声音——粗重、急促、像是破风箱在艰难拉扯,
每一次喘息都带着濒临崩溃边缘的嘶哑和粘稠的血气。那是…陈默的声音!
但那声音里浸透了我在他清醒时从未听过的、一种彻骨的恐惧和绝望。
“晚晚…”那声音艰难地挤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渗出的血沫,
“别…别开灯…”喘息声更重了,带着一种令人心胆俱裂的惊惶,
千万…别吵醒他…他就在…你身边…”我的名字——林晚——被他用这种濒死般的声音唤出,
像一根冰冷的钢针,瞬间刺穿了我的耳膜,狠狠扎进大脑深处。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猛地窜起,
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血液仿佛凝固成了冰渣。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僵硬冰冷,
牙关无法抑制地咯咯作响。因为我的丈夫陈默,此刻,就安安稳稳地躺在我身边!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体散发的温热,能听到他熟睡中平缓的呼吸声。
那规律的、带着一丝疲惫的鼾声,此刻却比地狱传来的丧钟还要恐怖。“陈默?你…你在哪?
你怎么了?”我压得极低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每一个音节都像是挤出来的,“他…他是谁?
躺在我身边的是谁?”巨大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我的心脏,几乎无法呼吸。
电话那头,回应我的只有一阵更加猛烈、夹杂着剧烈呛咳的粗喘,紧接着,
是几声沉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噗噗”声,仿佛有什么湿重的东西被用力捶打着泥土。
然后,“嘟…嘟…嘟…”忙音冷酷地响起,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紧绷到极限的神经。
通话断了。黑暗像凝固的沥青,沉重地压下来。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熄灭了,
最后一丝光源消失,卧室彻底沉入了无边无际的墨色深渊。我僵在原地,
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向了冰冷发麻的头皮,又在下一秒急速退去,留下彻骨的寒意。
身边的“陈默”依然熟睡着,呼吸平稳悠长,仿佛刚才那通来自地狱的电话从未响起过。
躺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念头带着剧毒的荆棘,狠狠扎进我的脑海,疯狂蔓延。
出差归来的陈默…他身上那股浓重得异常的泥土气息,此刻在死寂的黑暗中变得无比刺鼻。
那不是普通的泥土味,更像是某种…墓穴深处,
混合着腐烂根系和金属锈蚀的、沉积了千百年的阴冷气味。他带回来的那个沉重的行李箱,
就放在卧室角落的地毯上,像个沉默的、藏污纳垢的黑色棺椁。不!我必须做点什么!
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攫住了我。婚戒!我们的结婚戒指!
侧面刻着我们名字的缩写和结婚日期——“C&L 0421”。那是我们爱情的铭刻,
独一无二的身份印记。黑暗中,我屏住呼吸,像一条在冰面下潜行的鱼,
极其缓慢、极其小心地侧过身。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击着肋骨,发出擂鼓般的巨响,
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我生怕这剧烈的心跳会惊醒身边这个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我的手,
冰冷而颤抖,一点一点地,循着被子的轮廓,向着“陈默”搭在被子外的那只左手探去。
指尖终于触碰到他无名指上那圈冰凉的金属环。就是它!我强压着几乎要冲破喉咙的尖叫,
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腹,极其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摩挲着戒指的侧面。没有!
没有熟悉的凹凸纹路!指尖传来的触感光滑一片!不可能!我不死心,
指甲几乎要掐进金属里,更加用力地、仔细地感受着内圈的每一个细微弧度。终于,
指尖捕捉到了一点极其微小的刻痕!但那纹路…那感觉…完全不对!
那不是我们精心设计的缠绕字母!那感觉…像是两个方方正正的汉字!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字?汗水瞬间浸透了我的睡衣,黏腻冰冷地贴在背上。我拼尽全力集中精神,
尖神经末梢传递来的模糊触感在脑中疯狂地勾勒、比对…一个念头如同闪电劈开混沌的夜空!
“永爱”?不对!笔画似乎更多…是“永爱”后面跟了什么?一个姓氏?一个单名?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指尖的触感模糊得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几乎要被这模糊的认知逼疯时——“嗡…嗡…嗡…”一阵微弱、沉闷、却极其清晰的震动声,
毫无预兆地从卧室角落那个黑色的行李箱里传了出来!在这死寂得连呼吸都嫌吵闹的房间里,
这震动声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起一圈圈令人头皮发麻的涟漪。
那震动带着一种执拗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节奏,持续不断地从箱体内部发出,
像一只被囚禁在黑暗中的活物,正拼命地挣扎、撞击着箱壁,试图逃离。我猛地缩回手,
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身边的“陈默”似乎被这细微的震动干扰了,
呼吸的节奏极其轻微地顿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咕哝,身体微微动了一下。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全身的肌肉绷紧如铁,僵硬地维持着侧身的姿势,
连眼珠都不敢转动分毫,死死地盯着黑暗中他模糊的轮廓。时间在极度的恐惧中拉长、扭曲。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身边那沉重的呼吸才重新变得平稳悠长,
那令人心悸的震动声也终于停歇了。我像一尊被冷汗浸透的石雕,
在黑暗里又煎熬了不知多久,直到确认身边的气息彻底沉入深度睡眠,
才敢极其缓慢地、一点一点地从温暖的被窝里挪出来。双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
寒意瞬间从脚底直冲头顶。我踮着脚尖,每一步都踩在虚空里,生怕发出一丁点声响。
浓重的黑暗包裹着我,视线所及只有模糊的家具轮廓,那个放在墙角的黑色行李箱,
像一头蛰伏的怪兽,无声地等待着。我蹲下身,手指触碰到冰冷的拉链头,
金属的凉意顺着指尖蔓延。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压下狂乱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
屏住气,以最慢的速度,小心翼翼地拉开行李箱的拉链。
拉链齿分离的“嘶啦”声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每一声都像刮在我的神经上。
箱盖掀开一条缝,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土腥味混杂着铁锈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腐朽气息,
猛地扑面而来,呛得我差点窒息。
借着窗帘缝隙透进来的、城市远处霓虹灯极其微弱的一点光晕,
我勉强能看清箱内凌乱堆叠的东西。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几件卷在一起的、沾满深褐色干涸泥浆的衣物,散发着浓重的汗味和土腥气。衣物下面,
压着几件形状奇特、闪着冷光的金属工具——一把沾着暗红污渍的小型鹤嘴锄,
几根末端尖锐的探针,还有一把造型古朴、刃口却异常锋利的短柄洛阳铲。
这些工具上附着的泥土颜色深得发黑,像凝固的淤血。考古工具?陈默是考古学家,
这似乎正常…但那些深褐色的污渍…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的手在冰冷的工具和散发着腐土气息的衣物间摸索,
指尖突然触碰到一个硬硬的、四四方方的角。是一个皮面的笔记本?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抽出来。不是笔记本,更像是一本报告。
封面上印着几个模糊的烫金字体——《西郊柳河村汉墓群阶段性发掘报告》。
报告人署名:陈默。日期是…三天前?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三天前还在参与发掘?
那今晚回来的这个…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颤抖着翻开报告。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手绘的墓室结构图、器物清单。纸张带着潮湿的霉味。
我快速地翻动着,目光在潦草的字迹和模糊的照片上掠过,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线索。
报告末尾,一张对折起来的硬质照片滑落出来,掉在我冰凉的膝盖上。我捡起照片。
光线太暗,只能勉强看清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半身像。她站在一片荒凉的野地里,
背景是几座低矮的土丘,脸上带着一种…说不上是紧张还是兴奋的表情,
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头。这女人我不认识,完全陌生。照片背面,
用蓝色圆珠笔潦草地写着一行小字:“雅,柳河村北坡。等我好消息。——默”。雅?周雅?
这个名字像一道微弱的电流,
瞬间激活了我之前摸索戒指内圈时那模糊的触感——“永爱·周”?
难道戒指内圈刻的是“永爱·周”?这个“雅”,就是“周雅”?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后颈。我丢开照片,双手颤抖着,近乎疯狂地翻动着那本潮湿的报告,
纸张发出哗啦啦的刺耳声响。快到最后几页时,我的动作猛地僵住了!报告末页的空白处,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只有一行用深红色墨水或者…是别的什么液体?
写下的、力透纸背的字迹。那字迹狂乱、扭曲,
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绝望和诅咒般的怨毒:> **“若周雅未归,则全员殉葬。
”**“殉葬”两个字,写得尤其巨大、狰狞,像两只从纸页深处爬出来的血红色眼睛,
死死地瞪着我!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狠狠击中,瞬间一片空白。
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彻底冻结,停止了流动。全身的力气被瞬间抽空,
冰冷的报告从我僵硬的手指间滑落,“啪”地一声轻响,掉在脚边的地毯上。
那行血红的诅咒却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烫在了我的视网膜上,挥之不去。
周雅未归…全员殉葬…殉葬!
喘息…泥土的闷响…身边这个熟睡的人…他无名指上刻着“永爱·周”的戒指…所有的碎片,
在这一刻被这行血字强行拼凑起来,指向一个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真相!
就在我被这灭顶的恐惧彻底吞噬,思维完全停滞的瞬间——一只冰冷、沉重、毫无生气的手,
带着一种令人汗毛倒竖的触感,
悄无声息地搭上了我赤裸的、因为恐惧而布满鸡皮疙瘩的肩膀!“啊——!
”一声短促凄厉的尖叫无法抑制地冲破我的喉咙,又在下一秒被我死死咬住嘴唇堵了回去,
只留下胸腔里剧烈的抽气声。我像被滚烫的烙铁烫到,猛地向前扑倒,
手脚并用地向前爬开几步,才惊魂未定地转过身,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炸裂开来。黑暗中,那个本该熟睡的身影,
此刻正无声无息地坐在床边。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一个模糊而高大的轮廓,
像一尊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石像。他搭在我肩上的那只手,还悬在半空,
保持着那个诡异的姿势。死寂。令人窒息的死寂在卧室里弥漫,
只有我粗重得如同破风箱般的喘息声,和他那边…近乎于无的、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呼吸声。
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钟,却像一个世纪般漫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平稳,
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沙哑,却冰冷得没有任何属于人类的温度,
每一个字都像冰珠砸在地面上:“晚晚…”他叫我的名字,那声音钻进耳朵里,
激起一阵恶寒,“这么晚了…不睡觉…蹲在那里…”他微微歪了歪头,
黑暗中的轮廓显得更加诡异,“找到什么了?”他知道了!他一定全都知道了!
他看到我翻行李箱了!巨大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我的喉咙,我张着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徒劳地、剧烈地喘息着,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无法控制地颤抖。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尖叫:跑!离开这里!现在!就在我几乎要被这无形的压力碾碎,
准备不顾一切冲向卧室门时——“嗡…嗡…嗡…”我握在手里的、一直忘了放下的手机,
突然再次剧烈地震动起来!屏幕在黑暗中爆发出刺眼的白光,来电显示的名字,
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陈默!**是陈默打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那个刚刚在电话里发出濒死喘息、被埋在土里的陈默!
那个此刻正坐在我床边、用冰冷声音问我“找到什么了”的“陈默”,
也看到了我手机屏幕上闪烁的名字。他搭在半空的那只手,
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优雅,放了下来。黑暗中,
我似乎感觉到两道冰冷黏腻的目光,如同实质的毒蛇,缠绕在我脸上。接?还是不接?接,
可能会彻底激怒身边这个怪物,死得更快。不接…那可能是真正的陈默…最后的机会!
求生的本能和撕裂的恐惧在脑中激烈交战。手机持续不断地震动着,
屏幕上“陈默”两个字执着地闪烁着,像垂死者最后的呼唤。那震动透过冰冷的机壳,
传递到我汗湿的手心,像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倒计时。最终,
一股不顾一切的冲动压倒了恐惧。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颤抖的拇指猛地戳向了绿色的接听图标!屏幕瞬间亮起,刺眼的光芒驱散了眼前一小片黑暗。
视频画面剧烈地晃动、旋转,一片模糊的、令人作呕的土黄色占据了大部分屏幕。
光线极其昏暗,只有一点点不知从哪里透进来的、微弱的、惨绿色的光,